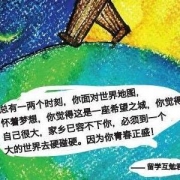埙是古人技法乐器,管乐器里边全世界最早的在全国6700多年以前出现的古乐器。在西安的半坡出土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就有该种乐器,那时候是将其用做打猎用的集合人的像号角一样的工具。当时只有一个一个小3度的孔,后来就发展到当做乐器来使用。商代的时候埙已经发展到五孔,该五孔以后就成为一种正式的乐器使用,但是由于五孔再也没有发展,明清时代埙就失传了。
地位
6000年前,半坡人在创造农耕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世界上最古老乐器--埙的雏形。在中国6000年的历史沉浮中,埙典雅优美的音色被沉醉于其中的封建帝王们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宫庭。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交替中,这种古老的乐器流入民间失去了文字的记载,逐渐从辉煌走向衰落,于明代开始成为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载。
出土埙
1956年,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了两枚距今6000多年的陶哨,它们用细泥捏成,保存完整,经过考古学和音乐家们的考证后陶哨被认为是我国最古老乐器埙的最早形式。
西安半坡博物馆宣教部主任李娟:在半坡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两件陶哨,考古家称为陶埙。这两件陶哨呈灰黑色,有一个孔两个音。
1977年著名的音乐家李骥先生,经过测定认为它是中国乐器埙的多体型。
演变
从半坡到汉唐,埙经历了由单音孔到多音孔的演变过程,逐渐形成能表达高雅、清丽、悲壮、深沉、凄凉之意的成熟乐器,被封建帝王们封为
"雅乐
" 盛行于宫廷。《诗经·小雅》中就有
"伯氏吹埙,仲氏吹篪(chi)
"这样的关于描写埙在古代宫廷盛典中的演奏情景。
由于埙从明代起就失传于民间,所以对二十多年前的现代人来说,相当多的人对埙是陌生的。
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上,一位名叫杜次文的北京青年男子用古埙演奏的古曲《楚歌》令所有在座的人为之惊叹,从此
"中国魔笛
"便成为埙的别称。从此开始引起民乐学术专家和民间艺人们的关注。
阴占中是陕西蒲城县平鹿乡的乡村音乐教师。十多年来因为喜爱古埙的音色,痴迷于埙文化的他,在自己家里设了一个手工作坊专门从事埙的研究与制作,成为陕西民间的小有名气的专业制埙人。
在这条遗留着古代文化韵味的古街上,埙已经变成了旅游商品跟陶质工艺品。但作为乐器,这些出自制陶艺人手中的埙,还不能够被称为乐器。它们只能吹出基本的音阶,不论是在音域、音色还是工艺制作上都不够规范。
埙的音色幽深、悲凄、哀婉、绵绵不绝,其声浊而喧喧在,声悲而幽幽然,具有一种独特的音乐品质。也许正是埙这种特殊音色,古人在长期的艺术感受与比较中,就赋予了埙和埙的演奏一种神圣、典雅、神秘、高贵的精神气质。埙和埙的演奏,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儒家礼教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把玩的乐器,埙是一件沉思的乐器,怀古的乐器。
经典的埙曲有《哀郢》、《长门怨》、《伯牙吊子期》、《长亭怨慢》、《高山流水》、《关山月》、《阳关三叠》、《苏武牧羊》、《山鬼》等,或演绎了中国的古典名曲,或专门由埙乐来演绎某种韵味,或用此来表达某种心情。几乎所有的埙曲都脱不了忧伤和伤感的干系,而某些埙曲借助它独特的音色,可以把哀伤演奏的荡气回肠,这是我听过的其它任何乐器都不能取得的效果。传统文人多性情者,也多有情绪化的忧思,埙本身独特的音色兴许恰好能反映传统文人这方面的气质,因而被很多传统文人所喜爱,却为布衣、寻常之民等所不齿,那些喜好热闹喜庆之人更不喜好听这种乐器。只为某些钟情于它者所喜欢。据考据除了一些独奏外,埙更多的是用在一些民间乐曲中,或者是在某些古典名曲中做个点缀的独特配角所使用。
我国古书上对埙的文字记载并不多。
《尔雅》注:“埙,烧土为之,大如鹅子,锐上平底,形如秤锤,六孔,小者如鸡子。”
《旧唐书.音乐志》说:“埙,立秋之音,万物曛黄也,埏土为之……。”
《诗经》云:“伯氏吹埙,仲氏吹篪。”
《诗经·大雅·板》形容:“天之牗民,如埙如箎,如璋如圭,如取如携。”
《乐书》说:“埙之为器,立秋之音也。平底六孔,水之数也。中虚上锐,火之形也。埙以水火相和而后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后成声。故大者声合黄钟大吕,小者声合太簇夹钟,要皆中声之和而已”。……
埙是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乐器
唐代郑希稷有《埙赋》道:“广才连寸,长匪盈把。虚中而厚外,圆上而锐下。器是自周,声无旁假。为形也则小,取类也则大。感和平之气,积满于中。见理化之音,激扬于外……”
这首《埙赋》对埙形状、大小、演奏,以及埙的声音都做了非常恰切的描述。说埙之声是“迩而不逼,远而不背”;“刚柔必中,清浊靡失”;“感和平之气,见理化之音”。众所周知,中国音乐文化浓厚的哲学理性精神和“以和为美”、重视潜移默化地培养人的审美情操的功能,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所以在乐器的制作方面,特别强调民族性。正所谓:“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埙就是一种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乐器。
虽然它的音量不大,最佳音域在两个八度之内,但这种气鸣乐器以其纯真、挚朴的音色而独具特色。因为埙的声音古朴典雅,与人说话时惯用的高频调相比,显得格外柔润。因此,适合表现人情味较浓的作品,尤其是一些质朴而感人的古典乐曲。如:辉煌的《哀郢》,表现了屈原魂断汨罗江时仰天长啸吟出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怀;描写楚汉相争,项羽闻四面楚歌与虞姬诀别的《楚歌》是为参加1984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第23届奥林匹克艺术节而作,由中央民族乐团演奏。这首乐曲充分发挥了埙的低沉,犹如人声的效果,把“别姬”的场面表现得极为凄美悲壮。洛杉矶奥运会后,乐团又在美国的十几个州巡回演出,开创了埙在国外演出的历史。外国音乐评论家指出:“埙几乎和中华民族一样古老,它那特有的音色,很是迷人。”当地报纸也有“此音只应北京有,人间那有几回闻”的报道。从此,埙这种古老而又年轻的中国民族乐器重新焕发出靓丽的青春。
埙是古代宫廷乐队的重要乐器
音色是埙之艺术美的体现。
埙之声,幽幽扬扬,深邃而悠远;厚沉凝重,幽静而淳厚。在周朝,人们依据制造材料的不同,将乐器分为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种,称为八音。而在这八音之中“,土音”乐器有缶、埙。缶是一种生活用具,也可作为敲击乐器;土制的吹奏乐器,就只有埙。八音包含的乐器为后世雅乐所专用,埙以其独特的音色和艺术表现力令金石以同恭,由此可见古人对埙的重视,并将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宫廷乐队和房中乐的重要乐器。
埙蕴含的儒家文化:质厚之徳,圣人贵焉
埙与篪的组合是古人长期实践得出的一种最佳乐器组合形式,由于埙篪合奏柔美而不乏髙亢、深沉而不乏明亮,两种乐器一唱一和、互补互益、和谐统一,因此被后人比做兄弟和睦之意,古诗云:“天之诱民,如埙如篪”,说的是上天诱导平民,犹如埙篪一样相和。“埙篪之交”也象征着中国古代文人的一种髙尚、髙贵的和纯洁、牢不可破的友谊。埙和埙的演奏,体现着中国传统的儒家礼教文化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唐代郑希稷在《埙赋》中说:“至哉!埙之自然,以雅不潜,居中不偏,故质厚之徳,圣人贵焉。”这就是说,埙所发出的自然而和谐的乐音,能代表典雅、髙贵的情思和雍容的气度,所以古代的圣人们是十分器重这种乐器的。
从《埙赋》中我们可以看出,从埙的成形到演奏已是涉及了哲学的深层领域,埙的品位由此已近极致。
埙,立秋之音
《旧唐书·音乐志》说:“埙,立秋之音,万物曛黄也”。
古人将埙的声音形容为立秋之音,更使我们体会到一幅朦胧而令人神往的艺术画面,秋天是万物成熟、喜庆丰收的季节。时光流逝,又有一种淡淡的悲凄和感伤。秋风扫落叶的现实,又使人平添几分愁绪。这就是埙的声音,这就是立秋之声音。它带给我们的不仅有收获的喜悦之情,也有“自古逢秋悲寂寥”的凄凉情怀。
《乐书》又说“埙以水火相和而后成器,亦以水火相和而后成声。故大者声合黄钟大吕,小者声合太簇夹钟,要皆中声之和而已。”它独特的音色,神秘的色彩,古朴典雅的风格,悲愁哀怨的曲调,是任何一种乐器所无法取代的。
埙是一件沉思、怀古的乐器
也许正是埙这种特殊音色,古人在长期的艺术感受与比较中,就赋予了埙和埙的演奏一种神圣、典雅、神秘、高贵的精神气质。
中国古人吹埙,吹了几千年,其声浊而喧喧然,寄托了古代文人雅士面对时光长河流逝如斯的失落感,但时光仍在无情地推进;中国古人吹埙,吹了几千年,其声悲而幽幽然,融汇了古代墨客骚人们对封闭而沉重的中国历史无可奈何的批判精神,但历史仍然在按中国既定的轨迹运行。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把玩的乐器,埙是一件沉思的乐器,怀古的乐器,这就难怪它“质厚之德,圣人贵焉”了。
部分文字摘自李翠萍《 埙文化的审美构成》
刘宽忍《埙演奏法》
埙赋 唐.郑希稷
至哉!埙之自然,以雅不潜,居中不偏。故质厚之德,圣人贵焉。于是挫烦淫,戒浮薄。征甄人之事,业暴公之作。在钧成性,其由橐钥。随时自得于规矩,任素靡劳于丹雘。乃知瓦合,成亦天纵。既敷有以通无,遂因无以有用。广纔连寸,长匪盈把。虚中而厚外,圆上而锐下。器是自周,声无旁假。为形也则小,取类也则大。感和平之气,积满于中。见理化之音,激扬于外。迩而不逼,远而不背。观其正五声,调六律,刚柔必中,清浊靡失。将金石以同功,岂笙竽而取匹?及夫和乐既翕,燕婉相亲。命蒙瞍鸠乐人,应仲氏之篪,自谐琴瑟;亲伊耆之鼓,无相夺伦。嗟乎!濮上更奏,桑间迭起,大希之声,见遗里耳。则知行于时、入于俗,曾不知折杨之曲。物不贵,人不知,岂大雅守道之无为?夫高则不偶,绝则不和。是以桓子怠朝而文侯恐卧,岂虚然也!为政者建宗,立乐者存旨,化人成俗,何莫由此。知音必有孚以盈之,是以不徒忘味而已。